首页 > 新闻中心组图 40年,我们一起走过 ——《读者》插图大型线上文献展 由旭声 卷
40年,我们一起走过 ——《读者》插图大型线上文献展 由旭声 卷

画插图的一些想法
由旭声
记得第一次为《读者》作插图是在1987年,当时刊物还没改名,叫《读者文摘》。
那年夏季,我按约定的时间去了出版社,当时我的同学在《读者文摘》做美编。坐定后他问我,给报刊杂志画过插图没有?我说画过,但很少。他说,给我们刊物也试着画画吧,但有言在先,约稿可以,画得不好可不能用啊,友善中带着原则性。
我接了两篇稿子,到家就迫不及待地研读起来,这活儿做起来是既有压力又感兴奋,凭着直觉和理解,还是顺利地画成交稿了。一月后街遇同学或同行,大家都已从刊物上看到我画的插图了,寒暄中多有鼓励。
第二次接的稿子是《唐纳德的梦》:一个工人,妻子是佣人,但他希望自己的女儿都能当博士。看过几遍后,脑海里便有了纷乱的画面,最多浮现的形象却是走来走去的企鹅,这些憨憨笨笨的形象,是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片《动物世界》里的片头场景,感觉正和文中我想画的几个孩子的形象相吻合,于是铺纸蘸墨,放笔直取,一张画便很顺手地完成了。后来这张插图参加了1989年的“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插图展览”。
接下来,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稿子交给我来画。每次拿到稿子,我都会兴奋,想着咋样才能画好。这样的约稿一直持续了许多年。
那时住在兰州大学的筒子楼,一间十来平米的房子里既是卧室,又是书房、画室兼客厅;厨房则是自家门口的过道,做饭时将灶具拉出。这时最热闹,家家门口一个厨师,相互招呼、说笑、调侃。有位老兄常常西装革履地弓腰炒菜,一手握铲,一手还要护着领带;楼上水房、厕所公用,脏得不便描述。一两年后,发现这幢楼几乎成为育婴楼,不知有多少婴儿在此诞生,仅起名叫龙龙的就有好几个。一晃这些孩子都上学了,考研了,读博了,工作了,成家了,出国了。如今,偶遇同楼的邻居,还会回味当年。最可回味的,对我来说,是许多插画能在那样并不好的生活条件下完成,这些画作今天看起来还带着那个年代的特殊气息。
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能为《读者文摘》作插图是很幸运的。这是因为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文化艺术氛围,特别是八十年代国内的文化热,使得兰州这座地处西北的城市有着同样的文化热度。兰州古称金城,是“丝绸之路”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镇,东临天水麦积山,西通武威天梯山、张掖大佛寺、嘉峪关魏晋壁画墓、 敦煌莫高窟,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分布在这绵延2000余公里的古道上。古和今,旧和新、传统和现代,都在这个城市里并存、生长、发酵、碰撞、融合。美术、诗歌、小说、音乐、电影、戏剧等各种门类的艺术思潮相继涌来,相互碰撞,许多画家、诗人及独立艺术家们,今天一个展览,明天一个聚会,常常是不同学科背景的人聚在一起讨论、交流、论辩,乃至口诛笔伐,热闹得很。
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一画画就满脑子想法。插图虽小且不独立,仅为文字的补充和延伸,那时却不甘心,就想着怎样把这小画画好让它有独立的感觉。于是画法、品位、气息、神韵、视觉效果成为我画插图时考虑的重点,在插画与文字的对应关系上也尝试了以下几种创作方法:
水乳交融法:力求与文字内容达到真正的交融和默契。有一些插图,单独看没问题,结合文字便看出尴尬:文字写实,插图却是抽象的表现;文字是哲理的玄思,插图却是现实的描绘;文字是幽默的调侃,插图却画得严肃而拘谨。与感受、与内容、与文体各方面融合,应是插图所具备的要义,达到此种效果,方能成为水乳交融。《资水河 我的船帮》插图遵循了这种方法。
若即若离法:好的插图应该是在忠于原文的前提下而不受其束缚,与其保持应有的距离。这样,插图就为文字打开了一个可能的空间,这个空间也许是文字表达的翅翼飞抵不到的地方,借助绘画语言,却可以引导读者走神——在这个新奇的空间中自由翱翔一番。如《大地非洲》的插图。
避实就虚法:以插图之“实”补文字之“虚”,竭力寻找能充分发挥绘画语言特性、自由表现文字引发联想的那个空间。文图相互生发,相互激活。从插图角度考虑,文字只是画的背景材料。我作插图的原则是尽量避开文字已呈现过的具体情节和画面,离象取神,造出窃以为好看、好玩、有趣并有生活依据的情境,其过程可称为再创作吧。《八美元的梦想》的插图如是。
貌离神合法:为意象性的文字所作的插图,最能体现这样的特点。表面看,文字的指向与插图的描绘没有太多的联系,有点“风马牛不相及”,但仔细品味,却能发现这类插图用心的良苦。为诗歌和格言画插图是让人头疼的:
闭上眼睛/把我关进你的身体/然后/让我睁开他们/看见水和光/飞鱼/看见自我······
——古马
你什么也不做,表针也在走。
——冯骥才
一个词,一个句子,形成多义的指向,若一对一地去画肯定是吃力不讨好,结果也定会南辕北辙。我的工作方法是在了解了诗人诗歌整体的创作走向后,撇开诗文,单独去画一组自己想画的东西。有意思的是,这些画和诗人的诗作放在一起并读,两者感觉却是出奇吻合。这个尝试使我明白了:插图与诗歌,尤其是现、当代诗歌的“对应关系”应该是以神似为目的才对味。见《牵挂》、《远方》插图。
给阳飏的诗歌配了这样的插图:天空无端落下几条鱼,三个长相相似、赤脚乱发、着装一致的女人自顾自地信步游走,亦梦亦幻,对应的诗句是:
这海太静太平了/这玻璃海/当它向西倾斜的时候/真害怕/我会一下子滑出地球边缘的/变一条鱼吧/睁着眼睡一会觉(鱼眼中的人是什么模样呢)/海盐/白了我的头发
数年后的一日,在网上看到了一段报道:
公元55年前,河南开封曾经下过一场谷子雨;1804年西班牙下过麦雨;19世纪初丹麦下过虾雨;1940年俄罗斯还下过一场银币雨;1960年法国下过蛙雨;1974年夏季,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天空忽然乌云密布,大雨倾盆,在暴雨中,1万多条鲈鱼从天空中降落……
这是想象的真,还是现实的幻?当我读到这段科学、客观的报道时,立时感到“真实”的索然无味了。是啊,画画可以不论科学,不讲道理,只要画面看上去有趣、好玩、令人遐想就行了。
但插图说到底是“命题创作”,离题的插图,即使画得再好,也会失去它原有角色的真正意义;而只求贴近文字,忽视了插图是一门再创作的相对独立的艺术,画作仅仅是文字的简单重复和再现,其艺术的内涵便会大打折扣,也失去了插图的可贵性。这算是那些年画插图的体会吧。
想想为《读者》画插图的那些年是充满了画画的快乐的。时而也会想起我喜欢写诗的父亲,他晚年坐着轮椅,外出“散步”时,还总要带上几本《读者文摘》——那里边有我画的插图,遇上熟人乃至并不熟悉的人,都要拿出来让人看看,炫耀一番。
2021.4.宁波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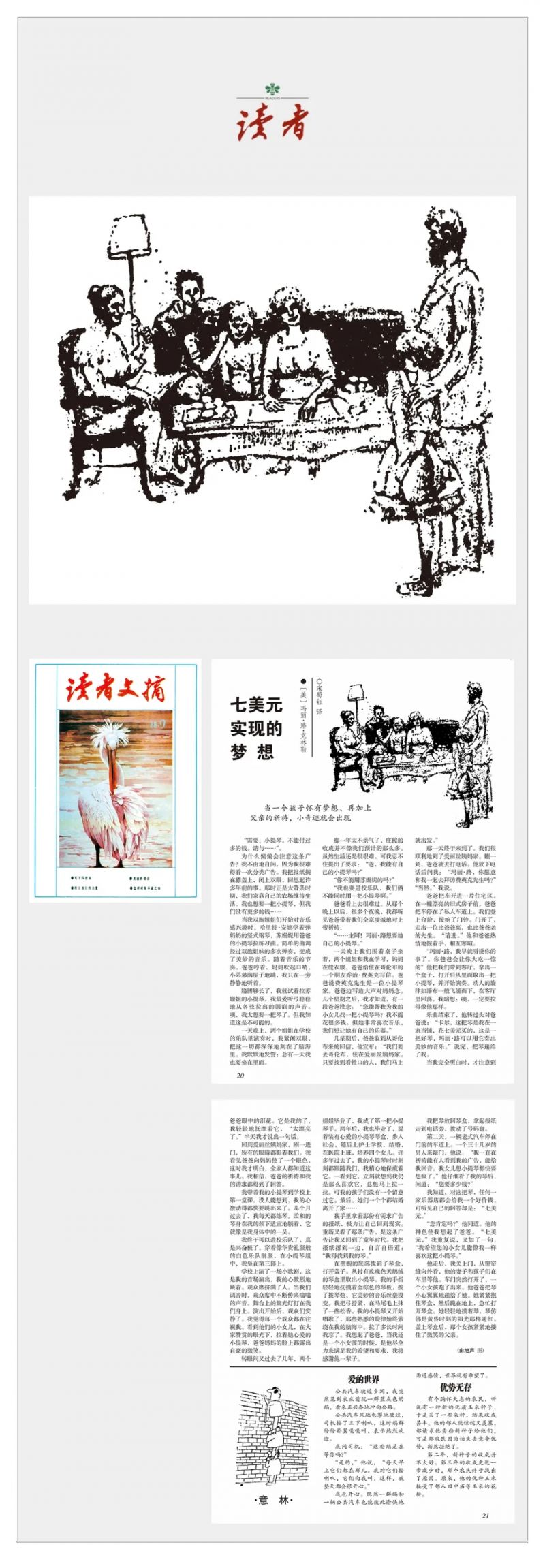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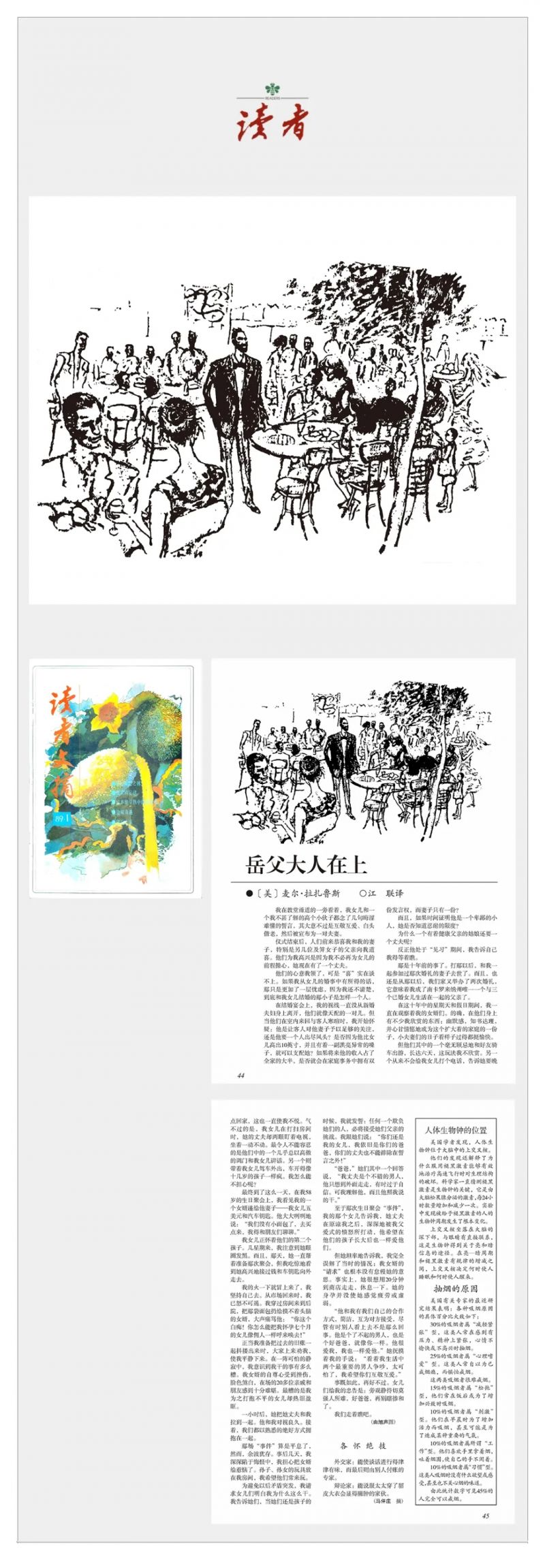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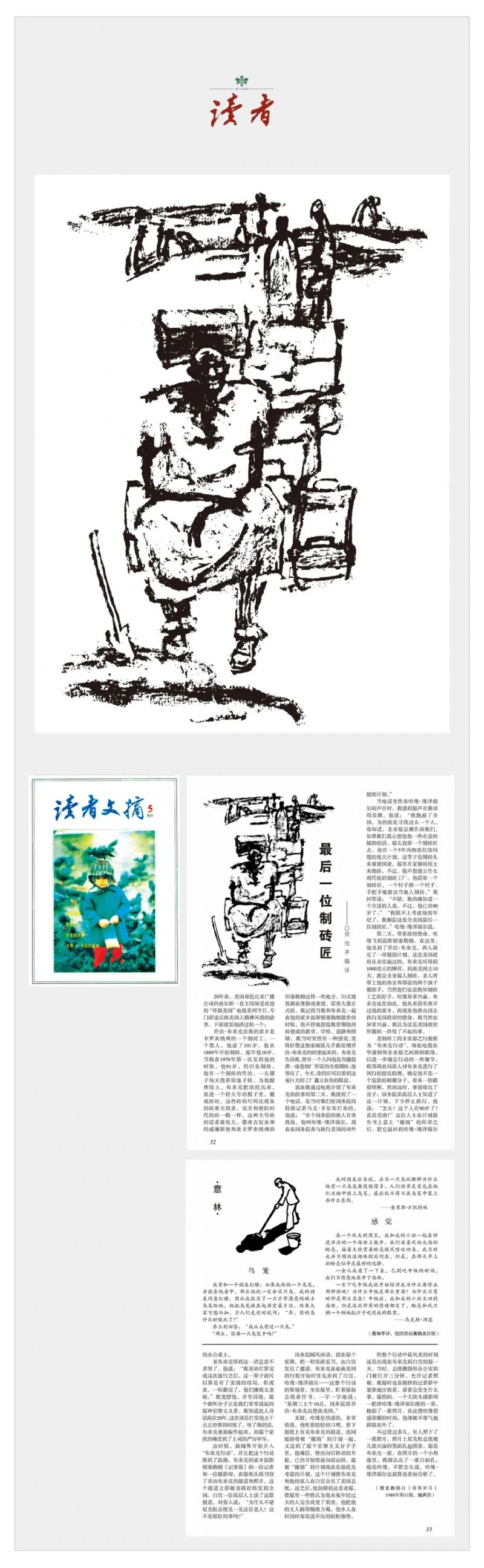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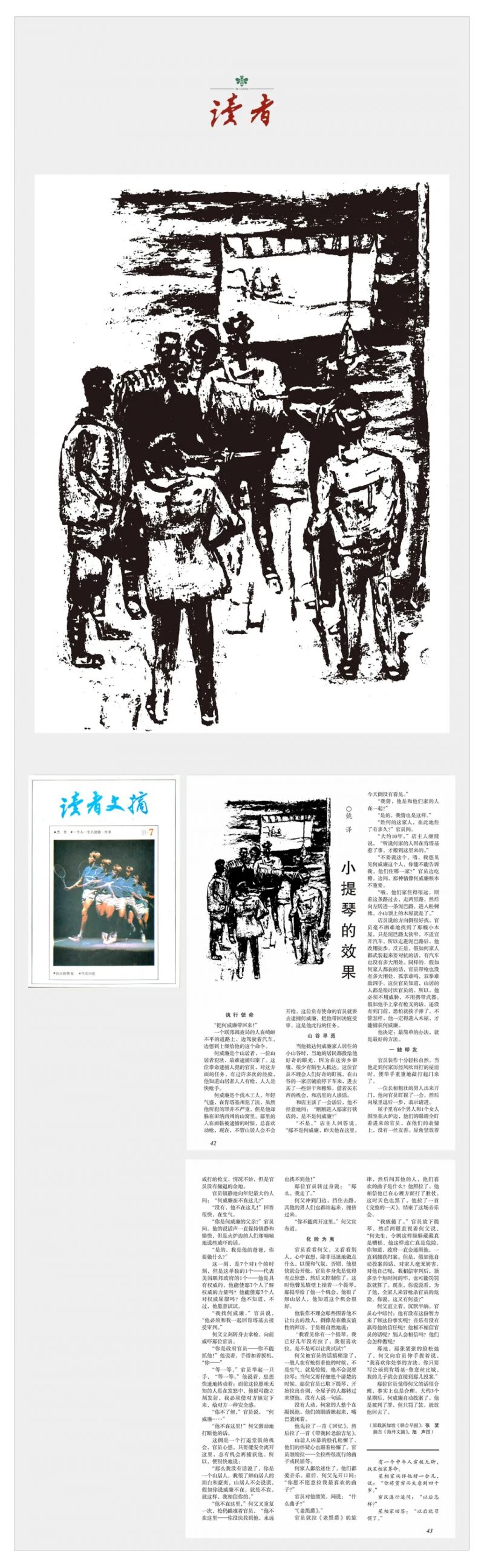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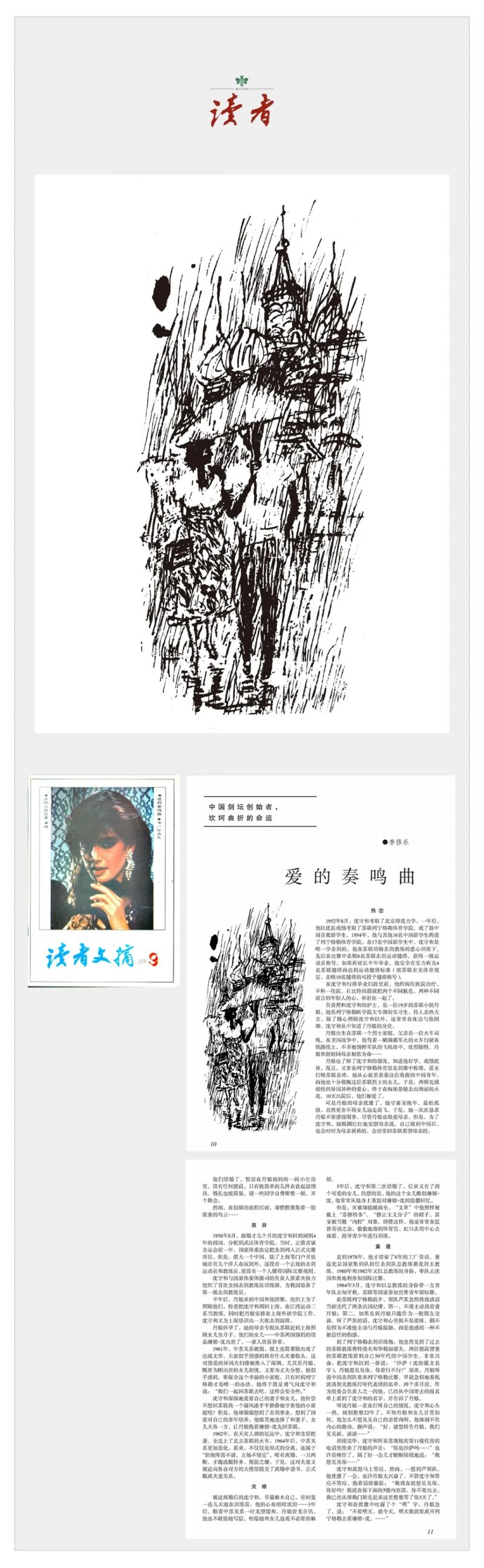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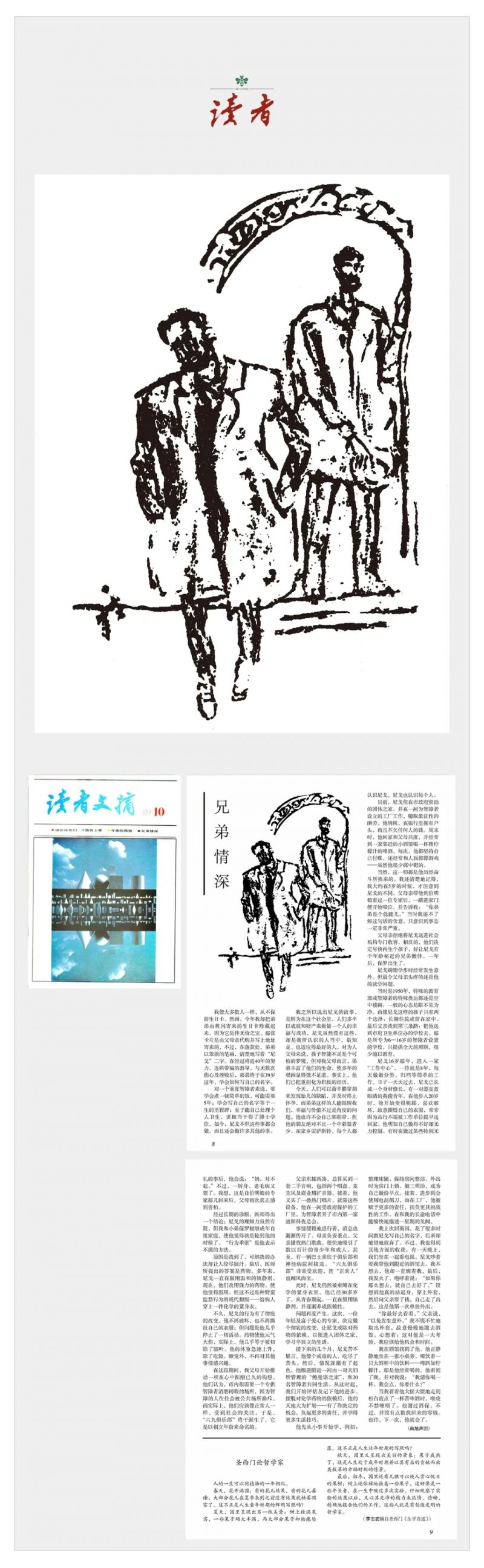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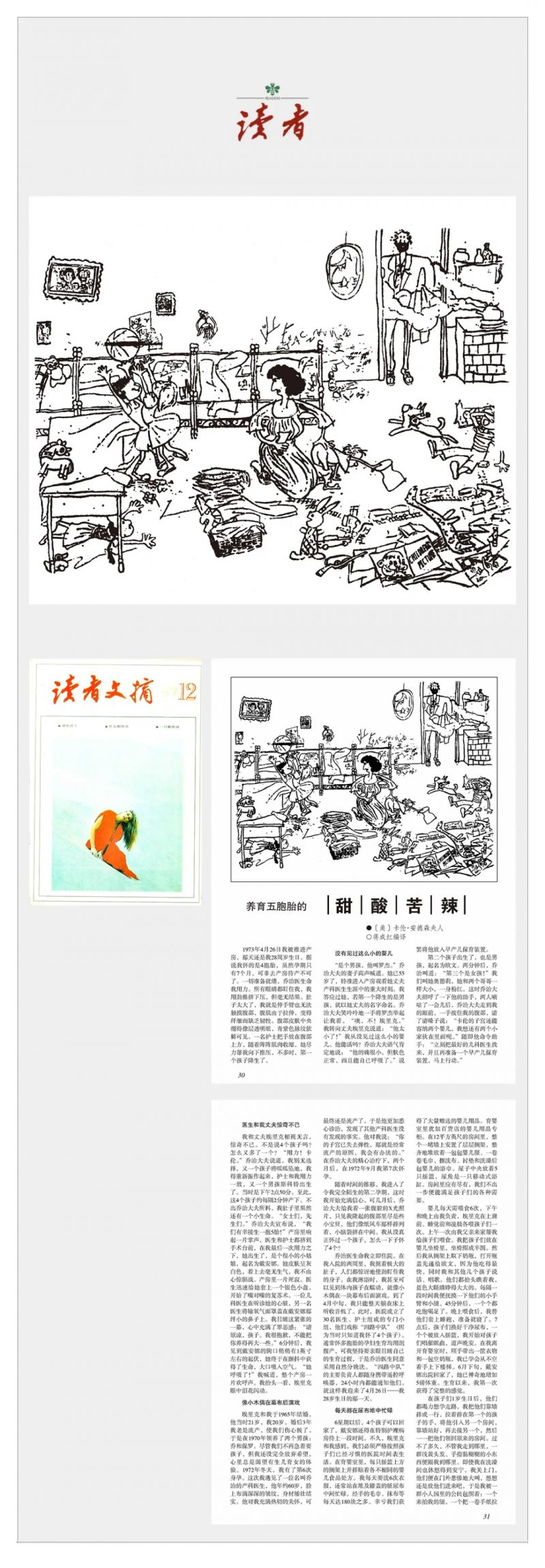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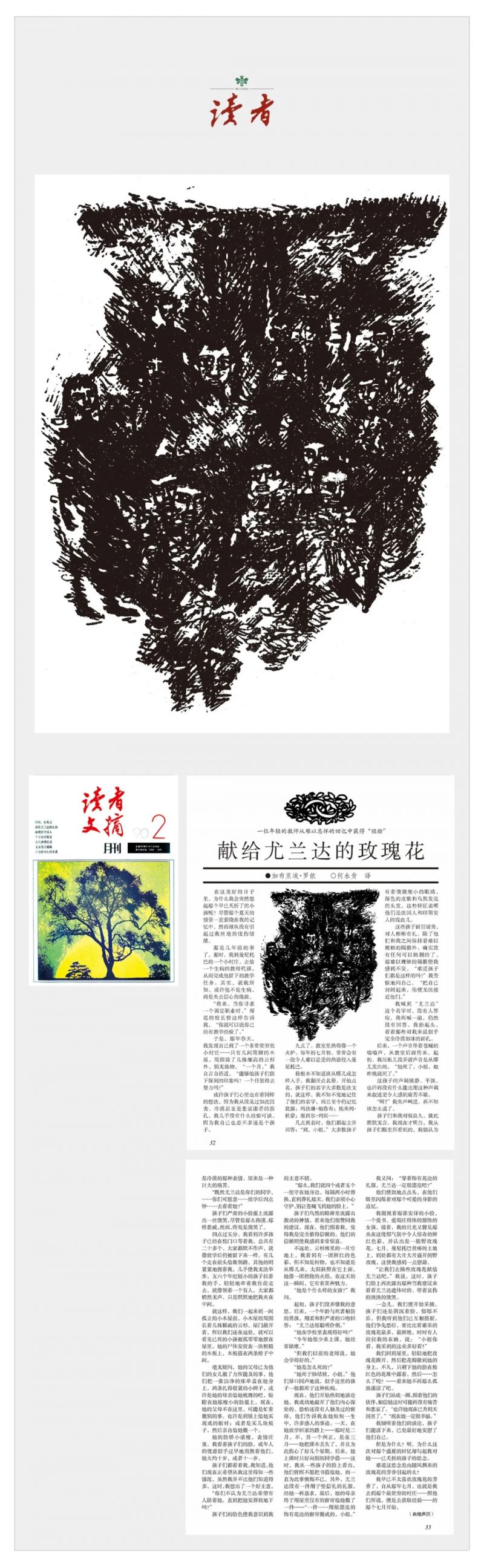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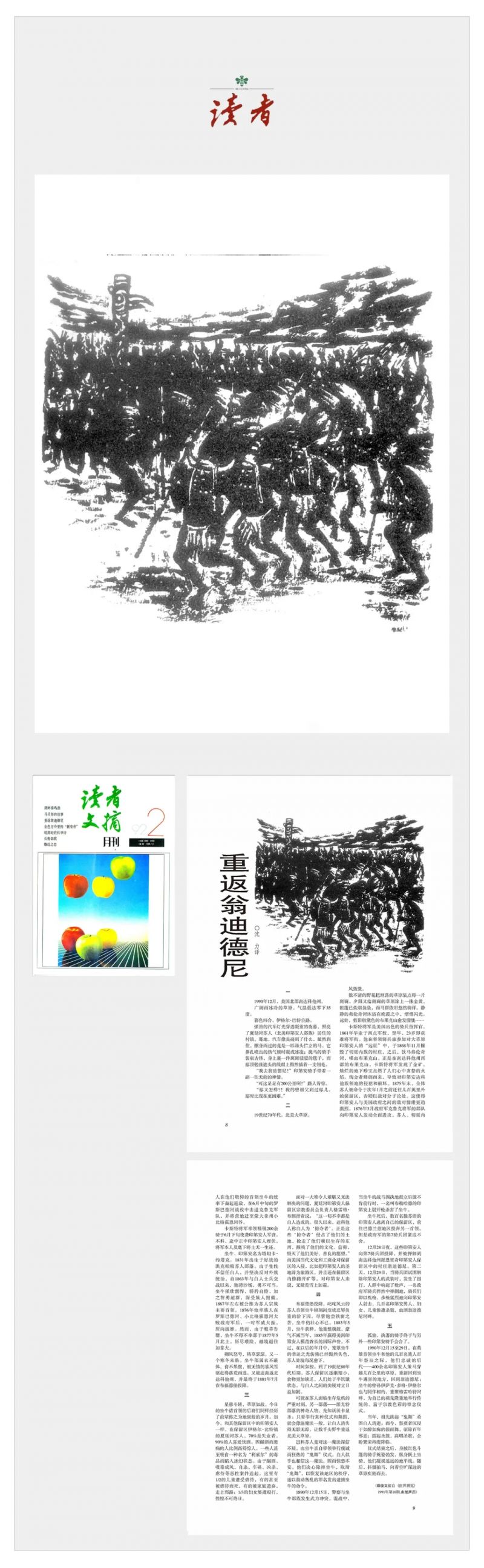

由旭声,1960年出生于陕西西安,1982年毕业于美术系,1993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助教研修班。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原传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,艺术设计研究所所长、教授;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;曾任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、艺术与现代设计研究所所长。
责任编辑:
文章来源:http://www.duzhepmc.com/2021/0805/1551.shtml
